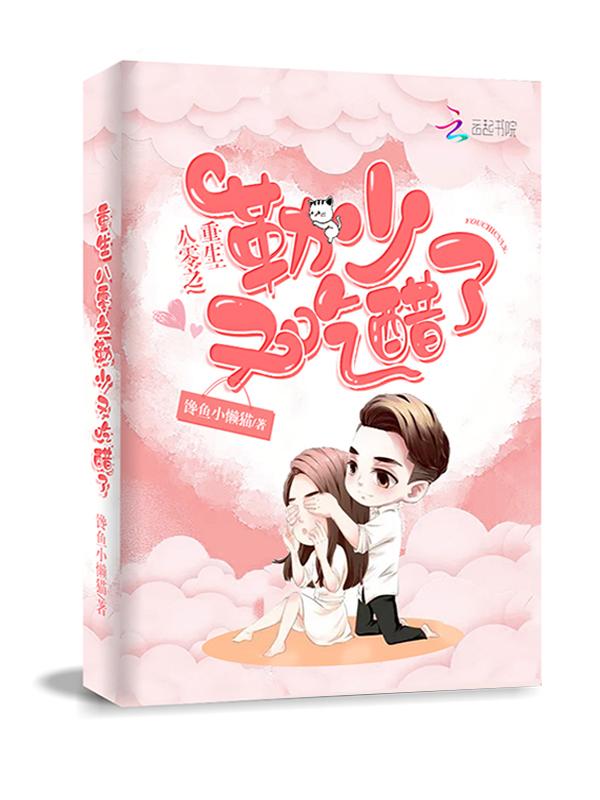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蕴他仙骨 > 90100(第10页)
90100(第10页)
自妇人游街叫屈,便是存着必死的决心,故而大夫诊出她早已服下七日之后发作的剧毒时,他与少君也没多少惊异。
既然以身为饵,少君又何必强留呢?倒不如纵她入局,好将这潭浑水搅得更浊些。
他们的少君虽是淮城的少君,可少君如此一个清风明月般的君子,又怎会谋害忠良之将?!分明是昏君的手笔!凭什么是少君背负千古骂名?
宋携青轻按眉心,一双眼落在他身上,淡问:“若我今日迟来半步,她便得落得个五马分尸,她虽已饮毒,然死,却不得全身,你以为如此,于将军在九泉之下是会对你感恩戴德还是怨入骨髓?来日,他们便会颂你为英雄么?”
他一想方才隐卫来报,江稚当街诛杀双生子中的兄长,宋携青隐有揣测,一叹道:“若于夫人此举可教他惶悚难安倒也罢,可你安知瀛国大乱不正是他所求的?”
响玉听不明白,他是瀛朝的君主,纵使平日荒唐,又岂会盼着江山动荡?
“响玉。”宋携青又是一叹:“素日里我对你多有纵容,你年岁尚小,我也不只是将你当作寻常下属,可在公事上,我到底是你的主子,是与不是?”
响玉讷讷点头,心下发紧。
“好,我既是你的主子,你却违逆我的意思,私放于夫人出府,响玉……”宋携青反问道:“我作为主子,还能留用你么?”
言罢,他也不等响玉回话,径直转身离去,“还是那句话,收拾好行装自去便是,还有,休在此处哭闹。”
屋里那人好不容易被他哄着睡下。
宋携青转出厢院,行穿在略显破败的小亭重楼直往后门,马车已备,妇人的尸身也已梳洗妥当,换上簇新的寿衣,沉眠棺中。
尸身是等不得头七再葬了,他太了解江稚,只怕他心思一转,又起了兴致,非得将尸首五马分尸,教人死后也不得安宁,至于葬地,便与于殊一道葬在郊外的密林深处,只须掩好行踪,便再无人可打搅二人。
宋携青决意同行,亲自送夫妻二人最后一程。
他随口问起孩子的状况,原也与翩翩差不离,哭累了便昏昏睡去,然而当一众正准备启程,那孩子却踉踉跄跄地追上前,死死抱着与他齐高的车轮道:“大人……大人我想送送母亲。”
子女送亲,天经地义,宋携青自然不加阻拦,只将半点大的孩子一把捞上马车,行途中,宋携青盯着不过五六岁的祈安,颇有深意地道:“回去后,抄四十遍千子文。”
祈安不明就里,碍于寄人篱下,他不敢多问,只得乖乖点头。
何况……阿娘曾说,他们是好人。
及至月破残云,一行人才将将安抵密林,祈安见宋携青行下马车,也忙跟在后头,连滚带爬地骨碌落地,放眼一望,早有仆从先行掘好墓穴,只待送葬的人一到,便可下葬。
祈安一头扑在棺上,纤瘦的小手轻抚还算精良的棺木,宋携青问:“可要再见见你阿娘?”
他只一见母亲,必难割舍,祈安皱着一张苦瓜脸直摇头,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掉,砸在棺木上,“多谢大人,可我不能再见阿娘了,见着气不喘口不言也不能睁眼看看我的阿娘,我……我会难过,阿娘见我难过,又怎么舍得同爹爹安心地去?”
宋携青不再多言,只吩咐人好生下葬。
随行的老木匠也已将墓碑镌好,匠人双手奉上,上刻:于夫人之墓。
祈安虽年幼,却已识得些字,眼下一见新刻的墓碑,泪水不由分说地决堤,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指着墓碑铆足劲道:“我娘才不叫什么于夫人!我娘叫向劲草!”
“劲草!”——
作者有话说:虽迟但大肥章
请给翩翩一点点时间[摸头]
第95章吃味
帝王罢朝半月,及至圣寿的第二日,文武百官才终于得见这位未及弱冠的少年君主。
江稚今日本懒于临朝,奈何边境急报如雪,加之宋琅连番上书敦促,他一日不上朝决策,急报便在御案上越叠越高,无法,江稚勉强顶着哈欠懒散地踏入金銮殿。
他高踞上首,听着一干臣子在玉阶下嗡嗡个不停,好比百来只蚊蝇。
所议之事,无非是大庆铁骑陈兵在边境蠢蠢欲动,而反观瀛国,粮秣匮乏、战马疲弱、国库空虚,甲胄枪剑非缺即劣……再及,朝中已无堪当大任的良将。
这也无怪,也就开国之初猛将如云,历经数代兵销革偃,后世的守成之君多喜阿谀逢迎善拍马屁的文臣,谁人还愿走武举之路?一来既无丰厚俸禄,二来无战功可立,倒不如做个巧舌如簧拍马溜须的文官,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封侯拜相。
直至先帝时与大庆战事又起,仓促间扶植将才,怎奈何……
阶下手持笏板的百官不约而同
地朝宝座上的昏君睇去。
在蠹虫蛀空的危朝之上,何人敢为将?
更何况……前些时日,不才死了个于殊?
是以,文武百官争论好半晌,仍无人拿定主意。
偏生今日帝师告病未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