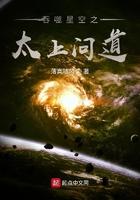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重明仙宗 > 第246章 义从暖堂消旧虑金丹斩捷振新声(第2页)
第246章 义从暖堂消旧虑金丹斩捷振新声(第2页)
这话言得有理有据,众修听得尽都赞同不止,却也让李二郎这火热的心又凉了一截。
蓝革清听着,端着酒碗抿了口,酒气顺着喉咙下去,见得堂内此幕倒是不甚意外。
他在堂县开了四五年的食珍楼,大小宗门弟子亦也得幸见过几位。以他所见,重明宗弟子却与平常大宗弟子稍有不同。
但也仅仅是有些罢了,他与堂中两个经年散修意见一般无二,却不信那位康大掌门当真是弥勒转世、修得一副菩萨心肠。
蓝革清有家有业,自也不会图应募散修那点儿卖命功劳,只是怕才安生下来的宪州再发动乱、殃及他这花了全部身家才置下的家当罢了。
要晓得,当年要不是鬼剑门被重明宗一战而下,令得依附鬼剑门的爪牙尽都被收缴了性命身家,不然似城门口这等通衢要道,他蓝革清一介散修怎么配赁得下来?
有了两个老修开启头炮,这堂中一时热闹起来了。
蓝革清正觉自己酒楼的隔音禁制或是都要遮拦不住,隐隐着急时候,却听得又有外客迈步进来。
抬眼一看,却是伙眼生的外乡修士。
那伙外乡修士刚迈进门,食珍楼里的议论声便顿了半拍。倒不是因为别的,只是这几人的模样,却是与寻常散修格格不入。
领头的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,约莫三十来岁,穿一身墨色灵纹法衣,料子是宪州少见的“云纹棉”,领口袖口绣着淡金色的流云纹,走动时纹路里隐有灵光流转,显是浸过灵力、请的正经灵裁制成的。
他腰间系着个鼓胀的法袋,袋口露着半截青钢戟身,剑鞘上刻着细密的防滑纹,虽只是件中品飞剑,却锃亮如新,一看就常用入阶兽油保养。
会使法器的修士尽都晓得这般精心蕴养的益处,然依着堂内一众散修看来,起码也得是筑基宗门出身的弟子,才会有如此豪奢。
他身后跟着几个同伴,衣着虽不如领头的讲究,却也都是有些浆洗得厉害的二手法衣。
几人进门时脚步沉稳,没有散修常见的局促,反而像回了自家地盘似的。领头那汉子目光扫过堂中,最后落在了蓝革清旁边那张空桌。
“店家,上四坛‘青雾酿’,若是有灵鹿肉,那便再切二斤、要卤得透的。”领头的汉子扫过堂中壁上挂着的食账开口、声音洪亮,没像堂县散修那样压着嗓子,完了又发言道:“再添几碟爽口的灵蔬,快着些。”
跑堂伙计愣了愣,连忙应着去了。
这青雾酿是食珍楼的招牌,一坛要两枚灵石,寻常散修半年都舍不得喝一坛。可这几人张口就要四坛,一顿饭吃下来足当得一般人一岁所得,出手真是阔绰得很。
在尽是穷酸散修落脚的食珍楼,倒是能算笔大生意。
王老栓眯着眼打量那汉子,手指在断袖上捻了捻,忍不住开口:“几位是外乡来的?”
领头的汉子转过头,见是个断了胳膊的老修,倒也客气,拱了拱手:“在下赵武,从云角州过来。这几位是我同乡,都是上宗义从出身。”
“云角州?义从?”这话一出,堂中顿时起了骚动。
李二郎猛地抬起头,攥着抄纸的手又紧了紧;张老木亦也凑了过来,眼神里满是好奇。
赵武见众人感兴趣,倒也不藏着,端起伙计刚送上来的酒坛,给自己倒了一碗,酒液入碗时泛着似几可忽略不计的暗弱灵光。
“侯爷当年还未结丹时候,我们几个就应过重明宗的募、当了义从。”他喝了口酒,咂了咂嘴,不觉滋味儿多好,可见得堂中众修模样,却是在面上生出一分矜色。
那王老栓颇觉讶异、但在迟疑一阵过后却还是不禁小心问道:“赵道友既是应募过了,怎么还。”
这老儿欲言又止的模样却是有些令人生厌,使得赵武卖弄心思亦都少了许多。
于是他便侧身过去不再与这老修好生讲话,只是认真吃起桌上灵肴,应付一声:
“这富贵、这道途,谁又嫌多?!尔等可不晓得在云角州应募是有多难。不讲了,我等食过这餐饭后就要去帐前听用,不好多言、还请诸位莫怪。”
赵武寥寥几字,却就令得众修若有所思,这时堂中一角却有句笑声传来:“我当为何尔等这般阔绰,原是断头饭呐!是该多吃些。”
众修听得此言,面上表情即也就丰富起来。
正在吃酒的赵武眉头一拧,他初来乍到、亦也不想生事,不过这时候其手下的年轻人却是沉不住气、亮了法器:“狗才你再吠一声?!”
那角落里头的修士亦是不做退缩,眼见得这堂内就要兵戎相见,最后却还是蓝革清这掌柜的出来,与双方都拜过一拜,方才轻声劝道:
“上宗是言城邑周遭十里,除生死擂上不得擅动刀兵,不然就要遭有司纠去处置,还请二位道友三思。”
这话冷言冷语那厮听过之后,只是冷哼一声,即就瞪过赵武一行过后这才迈出酒楼。